
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里通常是光辉伟岸、忍辱负重的形象,一如在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中用黑白影调营造出来的浓烈的情感体验。
但是这份感情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却发生了错位和位移,传统意义上的家长形象以及借助这个形象承载的那份厚重的亲情关系在他的作品中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和子辈的矛盾中不断改写和瓦解的失落的“权力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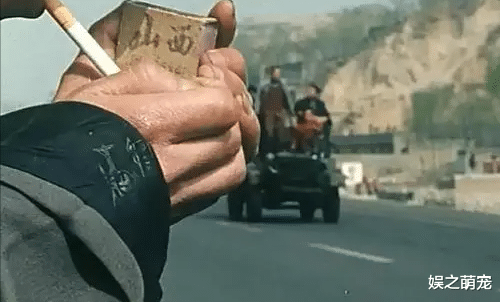
贾樟柯在电影中描绘了无数支离破碎的家庭版图。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贾樟柯在电影中营造了哪些家庭关系,以及身处其中的家庭成员的生存状态。
早在“故乡三部曲”时期贾樟柯就在《小武》中以一次“家庭会议”不欢而散的情节书写了家长权力瓦解的过程,并对这一过程造成的乡镇青年症候进行了深刻的描绘。

电影中因为老二张罗着要结婚的事情,所以父亲把老大和小武喊回家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由父亲担任这次家庭会议的主持人,而母亲在小厨房里烧水做饭,张罗着这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父母二人各司其职,分别担任着家事和家务上的“主持者的角色。
由父亲主持的家庭会议,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非常浓重的家族制社会的特色,贾樟柯在表现这一情节时,釆用了对比的画面效果,镜头正对着小武家卧室的一张炕,这张炕即是这次会议的“场所”,父亲一个人坐在炕的左侧,而另一侧坐着几乎全部的家庭成员——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准二儿媳以及小武。

此时的画面构图仿佛是一架天平,父亲说出的话的重量压倒了其余所有人。
父亲提到老二打算结婚的事,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态度“建议”老大和小武各出5000元用以资助老二婚礼,老大犹豫了一会儿表示说“拖拉机的养路费还没交,你让我从哪儿搞5000块”,小武见状也表示说“我没钱,我看老大的”。说完话小武就离开了炕(家庭会议的“会场”),原本"和谐”的画面突然失去了平衡,父亲的权威也因此失去了它在传统社会中应有的分量。

眼尖的小武突然发现二哥女朋友手上戴着的戒指是他之前送给母亲,让母亲保存起来以备补贴家用的,而此刻这枚承载着自己对母亲关心之情的戒指却出现在了老二女朋友的手上。
愤怒的小武来到厨房质问母亲,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小武:妈,我给你的戒指呢?
母亲:藏了。
小武:那你拿岀来我看看。
母亲:你不是给了我吗?
小武:我是给了你,但我没让你给别人!
此时,父亲冲了出来,边骂边作势要打小武。

父亲怒斥道:我看你是造反了吧!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养下你这个忤逆子弟,早知道在尿盆里淹死你!
怒火中烧但又十分委屈的小武绝望地离开了家,离开了一直压制他、让他备受屈辱的父权,一场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家庭会议也因为“戒指风波”而闹得不欢而散。
在现代性的洗礼下,父权的权威感已经不复往昔,父亲话语权的力量再大也敌不过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压力。

影片中父亲虽然要求兄弟二人各出5000元资助老二婚礼,但正如小武表示出的那样,没钱就是没钱,这种窘困的状态并不会因为父亲的权威压制而得到改善,走投无路的父亲和母亲打起了“盗用”戒指的心思,这枚原本由小武送给母亲当作礼物,此时却被用作订婚彩礼以强化家长在子辈面前的自我尊严。
这一行为非但没有让父母的形象得到巩固,反倒让他们的尊严崩塌得更为迅速和剧烈。影片最后,挣脱出父权“魔爪”的小武又重新回到了汾阳的街道上,他对自己父母的所作所为深感绝望,对自己的家庭充满了幻灭和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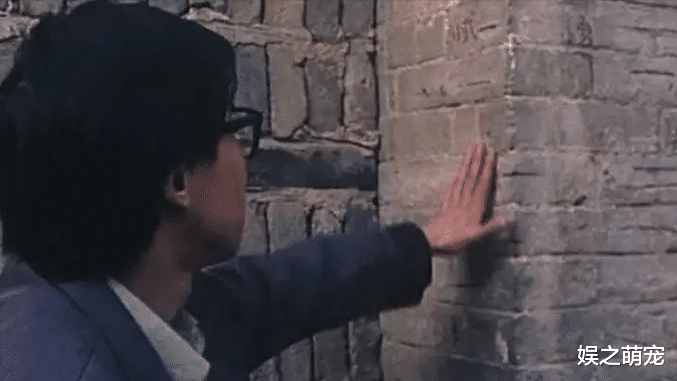
家长权力的瓦解导致了家庭职能的减少,电影中的许多乡镇青年们都不再视自己的父母为权威,家长的训诫和教诲再也不是颠簸不破的真理,“许多家庭职能都推向了社会……家庭的流动性增强了,家庭的物质需要相对削弱了,而对心理的渴求却大大增加了”。
失落的小武急于摆脱家庭的束缚,却未能习惯现代性的社会秩序和关系,极度渴望被认可的他只能重拾自己的老本行来寻找一些自我成就感,于是再一次偷窃的小武被警察抓获,他像一个融入不了现代性社会的怪物一样被周围群众不断地围观议论。

戒指本来是小武送给母亲的体恤之物,它承载着小武对于母亲的关心以及对于自己许久不回家而没有尽到孝道和责任的歉疚之情,这本应是凝结在戒指之上的深刻情感此刻却发生了位移。
作为戒指拥有者的母亲,将戒指作为一种信物转交给了二儿子的准未婚妻,它原本携带的亲情关系在被交到二儿媳手中的时候,便消失殆尽,随之一同消失的还有小武对亲子关系所寄托的温情。

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中消费者丧失了主体应有的主体性,消费品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牺牲人的利益的不合理的非人的主客体颠倒现象”。
在这里,戒指成为了一种“货币”或是一种“中介”,通过它小武的父母“买”到了二儿子的婚姻;戒指也由原来承载亲情的客体物摇身一变成为了小武家庭关系的主宰者,它一面勾连了一份婚姻关系,但同时也摧毁了一份父子亲情。

现代经济体制,金钱成为了一切关系衡量的标准,它夷平了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之间的原本应该普遍存在的丰富性,异化了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而金钱也最终打败了一切衡量标准,成为了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关系的最终表现形式。
这在齐美尔口中被称为的“文化悲剧”的主(人)客(金钱)体矛盾关系主导了贾樟柯电影中许多支离破碎的代际关系,现代性间或现代文化成为了摧毁原本稳固的亲子关系的元凶。

在第二部长片《站台》中,文工团工作的崔明亮自诩为文艺工作者,可以不用听父母的话,但他作为文艺工作者的“骄傲”却很快被母亲的一席话给贬损得一文不值。
在屋子里帮崔明亮改裤子的母亲嫌弃地讽刺他说:你一整天都没做事,就等着这裤子穿吗?
崔明亮略带“自豪”地表示:你咋不让老二干活?社会分工不一样,我是文艺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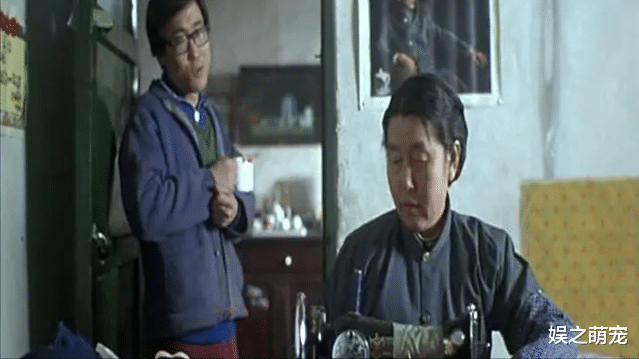
没想到他的母亲却回答道:文艺工作者?我不管你是什么工作,在家里就得听我的。
“在家就得听我的!”,这一句话从母亲嘴里讲出,没有用过于强调的语气但却掷地有声。
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只因为在家,所以崔明亮就必须得听母亲的,父母是家庭的主导者,哪怕他在社会上从事的职业是颇令人艳羡的文艺工作者。

小武和崔明亮只是贾樟柯众多作品中表达家长权力瓦解后果形象的典型,他们具有的共同特点是面对现代化冲击,家庭约束力迅速失落情况下的不安和无所适从。
他们渴望自我意识的表达和个体自由的解放,但因为家庭中父母权力的笼罩太过于持久使得他们无法短时间适应“父母缺位”的现代化生活,他们只能通过各种方法彰显自己的价值和实力,而结果往往和小武一样,成为一个离经叛道的“畸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