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论今年的白玉兰奖提名名单时,赵冬苓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编剧。她编剧的《警察荣誉》获最佳编剧(原创)奖提名,她改编的《幸福到万家》获最佳编剧(改编)奖提名。
《警察荣誉》在传统硬桥硬马的警察故事之外,开辟了一条生活化的创新之路,拍出了不一样的市“警”烟火气,塑造了广受欢迎的基层民警群像。《幸福到万家》为乡村振兴题材融入了精神文明和法治建设的视角,赋予了农村题材剧更立体的表达。

而翻开赵冬苓已经写完的待播剧,心里的敬意又会多上两分。《警察荣誉2》《警察荣誉·番外篇》《北上》《父辈的旗帜》《你好生活》《老家伙》《沙尘暴》……几乎部部为市场所看好。用观众的话来说,这都是瞅得见的好饼啊。
“全力以赴写现实题材,而且要带着提出真问题、表达真观点的态度去写。”这是赵冬苓一段时间以来的自我写作总结,应当也是其作品备受关注的原因。
在“降本增效”和“过会难”的整体趋势下,赵冬苓的创作为何推进得顺利而迅速?编剧如何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和现实题材的敏锐度?她的待播作品都关注到了社会的哪些横切面?

日前,我们与赵冬苓进行了一次连线,听她讲述近年来的创作思考。
《北上》:改编难度超乎想象
影视独舌:《北上》刚刚举办开机仪式,从小说到剧的过程顺利吗?
赵冬苓:《北上》是我写得很累的一个作品。从动笔到完稿,压力非常大,中间还住了两次院。
十多年前,我和姚晓峰导演合作过《叶落长安》,当时合作得比较愉快,于是这次他就希望由我来写《北上》的剧本。一开始就明确告诉我,要写当代的故事。
我有点懵圈,原著中有历史和当下两条线索。历史那条线写的是清朝的事儿,占了很大的比例;当代这条线写的是清朝那批人的后人在大运河申遗的背景下搜集文物的故事。

如果纯粹改成一个当代故事,就意味着编剧要重新写一个故事,但不要忘了,原著本身写得非常好,而且获过茅奖,要是放弃原著的主体故事,我编得未必有原来的好,而且书粉也不接受。
所以压力一直很大。后来我就跟姚晓峰导演一起到大运河边上走了一圈,回来后我又把视野放宽,把徐则臣老师(《北上》原著作者)的其他书拿来看。如果故事无法完全保留,那我想保留《北上》的气质和徐则臣老师文字中蕴含的魅力,这是我确定的改编方向。
具体到剧集文本上,《北上》是一部人物群像剧,写了大运河边上的六户人家,而且每一户人家都是父母双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主要人物起码有18个,每个人物都要有自己的个性、独特的面孔和独特的命运,这对编剧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影视独舌:原著精神内核要保留,故事和人物要大胆发挥,可以这样理解吗?
赵冬苓: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不可能摒弃原著,徐则臣老师笔下运河两岸的风情风貌也是非常宝贵的素材,都被融入到了剧本中。
剧本出来后,片方挺认可。我当时也跟他们说,一定要把剧本拿给徐则臣老师看一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不清楚他们征求了没有,所以心里一直比较忐忑。
《警察荣誉2》:年轻人的选择
影视独舌:您之前提到,《警察荣誉2》的写作灵感来自于一位B站UP主的吐槽视频?
赵冬苓:对。其实一开始没打算写第二部的,但第一部的成绩不错,从平台到观众都希望有第二部,我也很受鼓舞,但当时觉得很多问题在第一部里已经讨论完了,第二部还能写些什么呢?我一直没有找到切入角度。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那个视频,名字叫“年轻人的老去”。

我瞬间就被他的观点击中了。因为第一部写四个年轻人初入职场后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是怎么一步步改变的。这其实不光是警察,而是放在每个人面前的真问题:当我们走上社会的时候,会发现社会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是坚持做自己?还是做出某些方面的调整?还是被完全同化?这值得每个人深思。
答案是很复杂的,并不是完全坚持自我就一定对。因为你刚入职场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地方不成熟,确实该做出一些调整,而这种调整到底是被环境所影响呢,还是你在对现实有更多理解的基础上,主动为之?这是每个人的课题。
影视独舌:写之前重新采风了?有哪些新感受吗?
赵冬苓:写第一部的时候,我们跑了五个派出所,每个派出所开一次座谈会,然后很多故事就写出来了。
这一次呢,我觉得采访比第一次要充分,因为很多派出所的人都看过《警察荣誉》了,而且非常喜欢和认可,所以他一开始就很信任你,非常热情地提供他们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经历和所思所想。这让我对派出所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影视独舌:《警察荣誉》番外篇是在采风过程中形成的吗?
赵冬苓:其实我最早想写的就是番外,因为我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重点在四个年轻的警察,没太大的精力和笔墨去写四位师父包括王守一(王景春 饰)他们的过往,但想必观众也能感受得出来,他们都是很有故事的人。
所以有了这个机会后,我就想把他们的前史好好地表现一下。比如,曹建军(赵阳 饰)怎么会成为曹建军?王守一是怎么当上所长的?就是写十年前的八里河,我觉得蛮好玩的。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16集的剧本,目前的话,正在根据平台那边的意见,做进一步的修改。

影视独舌:演员方面,有望实现原班人马吗?
赵冬苓:我个人来说肯定希望,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新问题,只能说尽力而为吧。番外篇凑齐几位老同志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它本身比较短,操作起来难度会小一点,而且我觉得他们都会喜欢番外篇的。
影视独舌:《警察荣誉》是在观众的呼声和平台推动下启动的第二季,这对您有哪些启发?以后的创作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有系列化的规划?
赵冬苓: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努力在其他剧布局系列化了。我在爱奇艺有一个项目叫《你好生活》,是律政题材,已经拍完了,现在正在做后期。这部剧从一开始就是按系列剧来规划的,所以第二部我也早就写完了,可能第一部播出后,第二部也就要开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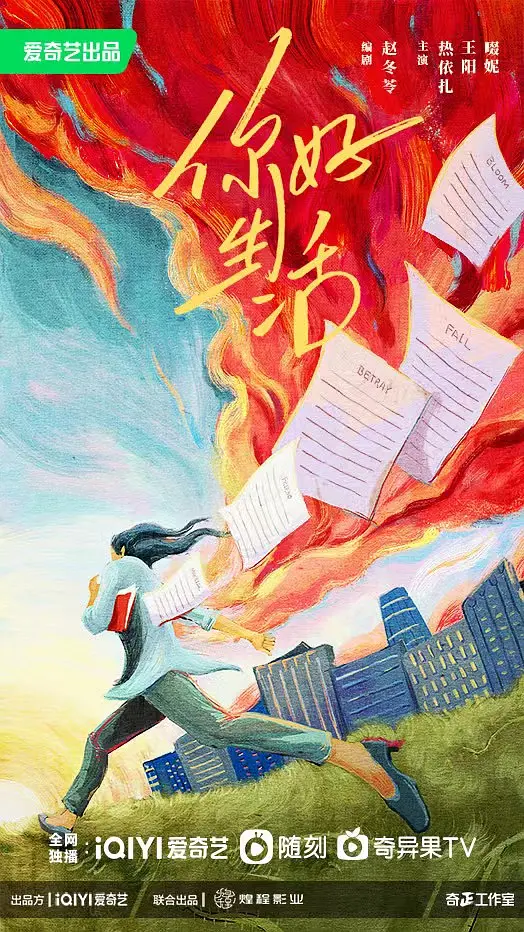
我一直试图找到适合季播的题材,找来找去还是觉得律政剧最合适,编剧把人物设计好,不断有案件进来,它就适合一季一季往下走。但想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你不可能把里边的主要人物当成工具人,他们也必须随着集数的推进有相应的变化。所以一直在尝试,也值得试,我也非常感兴趣。
影视独舌:按这个思路,《警察荣誉》不是更适合吗?第一季人物塑造很成功,后面不断有案件进来就可以了。
赵冬苓:还是那个问题:人物要有变化。《警察荣誉》我一开始就没打算写第二部,所以我几乎把他们在一个阶段的成长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不可能把他们当成工具人,只管破案,只管处理那些鸡零狗碎的案件,所以规划很重要。
《沙尘暴》:被现代文明遗忘的小城
影视独舌:《沙尘暴》也开机了,这部剧好像比较神秘。
赵冬苓:这部剧筹备的时间很长,其实我一直对悬疑剧是很有兴趣的,《沙尘暴》可能只是我尝试的第一部,以后还会继续拍,现在光写完的剧本就有两三部了。
这里边的案子最早是我去最高检做采访时,听最高检的一个检察官跟我说的:一个锅炉里掉出了一具尸体。

当然最后写出来的故事版本可能那位检察官看了也认不出来了。我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了一个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边陲小城,里边的人有的想走出去,有的想固守在这里,由此产生的一些冲突。有个演员非常想争取里边的一个角色,他就给我来电话,说剧本里写的生活他太熟悉了。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故事也能感染到很多普通观众。
除此之外呢,我希望通过这部剧致敬《冰血暴》,做成一个比较风格化的作品。
影视独舌:您说对悬疑剧很感兴趣,那最近有看《漫长的季节》吗?
赵冬苓:有看。我觉得这部剧的出现对我们所有的从业者都是一个提醒,或者说是启发。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不把破案当成故事的第一要义。后来我想想,如果我来写这个悬疑剧,我不敢这么写。导演一定是有强大的内心、强大的自信,才把塑造人物、书写那个时代大潮下小人物的命运当成了主要任务。你想是不是这样,看前三集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案子,一直在写那几个人物。

它的出现对平台也是一种启发。平台以前想要什么样的悬疑剧,它会希望你第一集死个人,第二集再死个人,通过强刺激去吸引观众。而《漫长的季节》完全不考虑这些,它的案件很缜密,很细致,同时又充满了同情和悲悯,并得到了观众的认同。
起码对创作者来说,如果以后平台还想提那种强刺激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拿《漫长的季节》来说事儿了。所以我说,它的成功对悬疑剧这个类别、对行业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
《老家伙》:披着老年题材外衣的青春热血剧
影视独舌:《老家伙》集齐了最具知名度的铁三角: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这算是从演员层面造了一个高概念吗?
赵冬苓:你可以这么说,因为确实是想到了这三个演员才有的这个项目。这部剧是当年山东省委宣传部的部长给我下的一个任务,他说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很受关注,所以就希望我写这么一个题材。
我一开始有些排斥,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这个题材真的有人看吗?后来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铁三角”,于是我就跟张国立打了个招呼,他一听很高兴,也非常积极,所以这个项目实际上从一个字儿都还没有的时候就先定了这三个演员。

除了演员的选择,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披着老年题材外衣的青春热血剧,因为如果只是写老年问题,写一个人如何老去,观众基础还是存疑的。
影视独舌:是不是喜剧化了?
赵冬苓:有喜剧的特点,然后他们的人设和以前的作品保持一致。我写完剧本后发给他们,他们自己就把角色领走了,不用说就知道要演的是谁啊。
影视独舌:听起来是把老年人当年轻人来写?
赵冬苓:是这个意思,跟年轻人一样谈恋爱,跟年轻人一样去做各种事儿。当然也会有其他年轻的角色,但重点是放在三位老同志身上。

影视独舌:平台对这种剧是什么态度?
赵冬苓:一开始我也担心平台不接受,但实际上爱奇艺看了后还挺接受的,毕竟它不是一板一眼的老年题材,而且还有这三位演员坐镇,他们应该在各个年龄段都很有影响力,很多人真的是看着他们的剧长大的。
《父辈的旗帜》:人与自然的相处
影视独舌:《父辈的旗帜》好像也蛮久了,现在到哪一步了?
赵冬苓:现在应该在做后期,好像不久之后就会启动宣传。
这个剧的创作过程也比较有意思。大概是两三年前的9月份,内蒙古有关方面给我打电话,说希望我能写一个有关林业转型的剧本,而且还跟我特别强调了,如果想采风就要快点来,因为要去的那个地方叫根河,有“中国冷极”之称,最低达到过零下五十多度,再晚就进不去了。
前往根河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林业转型到底应该怎么写呢?难道写下岗再就业?应该不会有人愿意看吧。直到开始采风,这个困惑仍然没有解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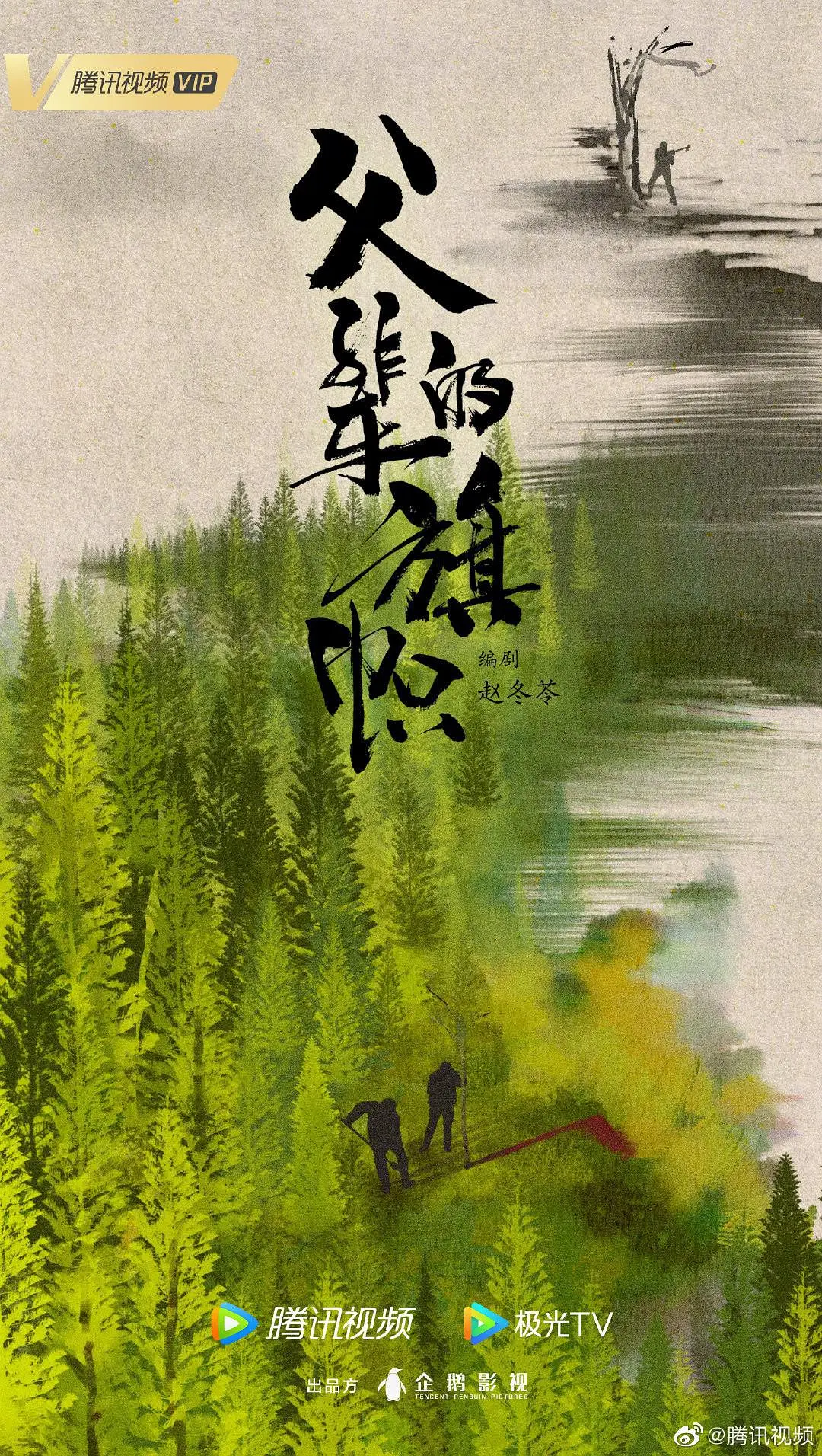
有一天,我到一个工队去参观,在那吃饭时下了点小雨,我就站在餐厅门口避雨。这时候,当地一个陪我参观的人走过来,说赵老师,您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我就跟他过去了。
那是一个景点,有两棵树,一棵已经被伐倒了,另一棵还站在那儿,旁边立着一个牌子,上书“最后一棵树”。他告诉我,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早在2015年开始,就挂踞停斧,全面停止一切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实现了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看着那两棵树,被伐倒的那棵还保持着原有的模样,而站着的那棵显然已经粗了一圈,我的内心瞬间就被击中了,觉得什么都有了。
我想我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就是中国人和自然相处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过去我们一直在向大自然索取,攫取资源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但现在我们停止采伐,转而去养护他们。这种变化,是林业工人做出巨大牺牲换来的。
他们不再伐木了,变成了护林工人;他们原来收入很高,但现在很多人可能失去了工作;他们以前技能高超,现在可能无用武之地了。

所以为什么叫《父辈的旗帜》?因为他们是在中国林业转型过程中无私奉献的一群人。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写什么,但我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面貌,他们如何在转型过程中相濡以沫、相互扶持。这太动人了,所以我写剧本的时候,实际上动了真感情。
影视独舌:精神内核在这里找到了,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是怎么来的呢?
赵冬苓:采访过程中都遇到了。我一直觉得,有些事情如果不是亲眼见到,就算最会写故事的编剧也不一定相信。比方说剧里有个主人公,因为被虫子咬,导致肝坏死,后来换了肝。那么这个医药费是怎么来的呢?是当地的林业工人凑了几十万,帮他度过了危机。也正因为如此,他放弃了从家乡走出来的机会,选择留在家乡,报答那片土地。
这个故事不是我编的,而是亲眼见到了那个人,所以写的时候完全相信,我希望观众也能相信。
影视独舌:《警察荣誉2》、番外篇还有《老家伙》《你好生活》《北上》都是爱奇艺的,《父辈的旗帜》是腾讯视频的,《沙尘暴》是优酷的。在行业“降本增效”和“过会难”的趋势下,您的项目好像不曾受到影响,推进一直很快。在跟平台的交流上,您都有哪些心得?
赵冬苓:以前是跟电视台合作,后来慢慢变成平台,对我来说肯定也是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别人一开始拿着我的剧本去跟平台打交道,平台也会有所疑虑,毕竟我的年龄放在这儿,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符合平台气质。我身边的人也会说,你的剧本拿到平台,让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小孩评头论足,内心不会抗拒吗?

我想说这对我从来都不是问题,一是时代发展到这儿了,作为创作者就必须去适应,否则你就被淘汰了。二是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作品在平台那就有多大的把握,但我自己会对剧本有很高的要求。曾经有一个项目,平台已经过会了,但我改到最后也没有过自己这一关,所以又把它收回来了。
我觉得只有这样,你才会对提交上去的剧本有信心。编剧么,归根结底还是靠作品、靠口碑说话。
【文/许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