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政界、媒体和公众中流传的词:“同情者”。
这不仅意味着那些在地下向英国皇家空军提供金钱、武器或文件的人,更意味着“恐怖精神先驱”或“媒体准备者”。
与“帮助者”或“支持者”不同,这可以随意延和打击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敢于要求对斯图加特 - 施塔姆海姆的囚犯进行人道待遇,例如与他们交谈寻找“迷失”的人,以及那些批评国家的人。其中的人物与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和彼得·施奈德不同,关于这种现象可能有两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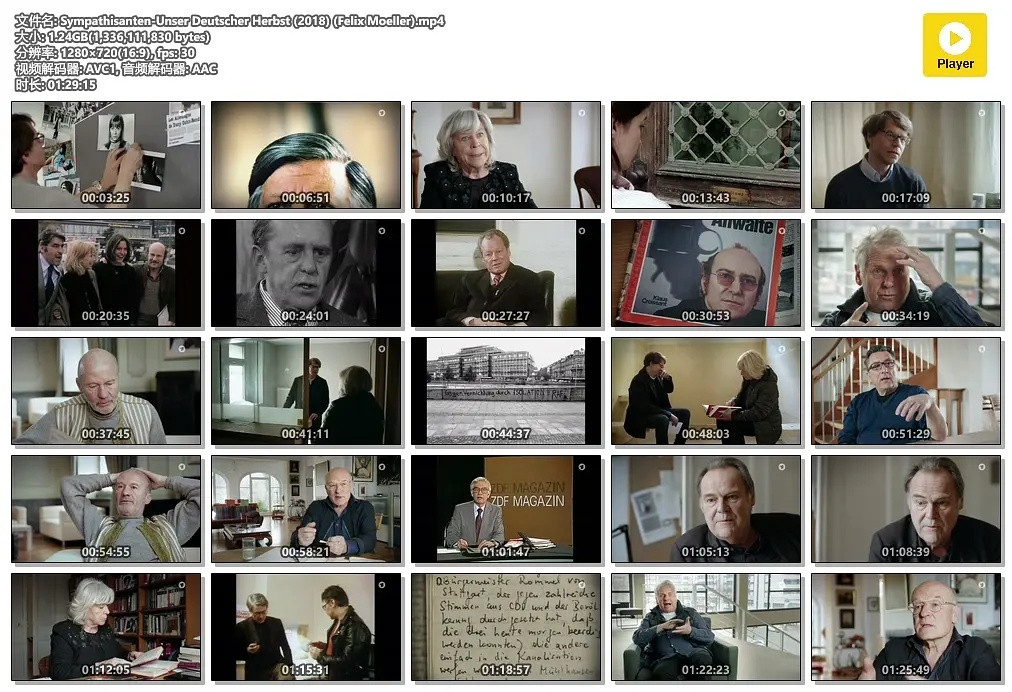
一个国家,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允许自己被一小撮地下斗士说服,违反法律和规则,以表现自己是一个“强国”和一个耸人听闻的人。包括公共广播公司的一些煽动者,已经升级为一种追捕和谴责的心态。“同情者是媒体的发明,”René Böll 说。在这个故事中,1977 年的死者直接或间接成为国家暴力的受害者。在另一种说法中,地下分子在引诱一些“自由派白痴”为他们游说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尽管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在他们的杀戮行为中,他们始终在语言和行为上回归到他们最初想要与之抗争的法西斯主义。在这个故事中,霍尔格·迈恩斯在绝食后的死亡只不过是一种特别激烈的宣传形式。真相可能不在“中间”,而是在两种叙述的辩证关系中。

可能再也无法详细揭开。正如丹尼·科恩-本迪特 (Dany Cohn-Bendit) 曾在本片中所说,双方“都对真相不以为然,无论是同情者还是国家,”这可能是上个世纪最轻描淡写的说法之一。Felix Moeller 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纪录片作家和制片人,自 2003 年以来,他一直在制作自己的纪录片,讲述电影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包括关于早期的希尔德加德·奈夫、维特·哈兰或国家宣传的“禁片”) ,并且是玛格丽特的儿子冯特罗塔和沃尔克施隆多夫的继子,可以说,三度注定要寻找这个词,这在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的生活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家族史和社会史因此在影片中反复重叠,由对话、当代文献和电影节选组成,但也包含一个非常微妙的旅行动作。

影片以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的演讲开始,他在演讲中谈到了恐怖分子必要的“道德孤立”和“甚至是最后的同情者的道德幻灭”。最后,我们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再次看到这个赫尔穆特施密特,他在采访中拒绝使用“同情者”这个词,因为它太“模糊”了。在陷入了新闻档案之前引起了很多恶作剧的想法的括号。中间是 Christoph Wackernagel 和 Karl-Heinz Dellwo 的声明,他们已经转入地下,Dany Cohn-Bendit 和 Peter Schneider 拒绝恐怖,René Böll 谈到了他父亲面临的敌对行动,Marius Müller-韦斯特哈根 以演员歌手的身份陪伴德国的秋天。在历史录音中,我们遇到了海因里希·伯尔、威利·勃兰特、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摘录自 »克里斯塔·克拉格斯 (CHRISTA KLAGES) 的第二次觉醒« 至 »凯瑟琳娜·布卢姆 (KATHARINA BLUM) 的《失去的荣誉》 (LOST HONOR) « 展示了新德国电影应对暴力和谴责气氛的尝试。

最后,2017 年关于德国秋天的纪录片与克鲁格、施隆多夫和法斯宾德 1977 年的联合作品融合在一起。随着几年来“同情者”一词的膨胀传播以及所有因某种原因被指控的人的国家和新闻界待遇,战后德国社会首次划定了一条激进的断层线, Oskar Negt 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排斥的意图:»同情者不是支持者,我们都是同情者«。最后,攻击的方向很明确,比如马蒂亚斯·沃尔登在电视评论中就针对“多年来出版印刷品的出版商”,而在联邦议院,他们甚至说知识分子同情者的责任甚至比肇事者自己的责任更大。Marius Müller-Westernhagen 今天认为但是,尽管寻求“公民社会争端的警察国家解决方案”引发了愤怒,但赫尔穆特施密特所说的幻灭是不可避免的。

彼得施耐德特别自我批评地指出,已经完成了害怕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胆小鬼”,害怕做出实际上在道德上无法合法化的姿态。人们不会期望一部具有这个主题的电影有太多正式的电影野心。它与通常的电视纪录片的令人愉快的区别在于它研究和倾听的耐心,摒弃了万事通的评论,同时主观视角的开放,面对矛盾的勇气。“我不确定我现在是否理解了更多,”电影制作人说,不,我们观众也不能确定这一点。但视野变得更广、更精确,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一次又一次,似乎直接针对我们现在的情况和陈述闪现。例如,Volker Schlöndorff 当时在法国电视台解释说:»这是一个无法忍受自身内部任何矛盾的社会,它不得不创造一个外部敌人,一个边缘人物,这样你就可以投射你所有的恐惧、仇恨和不满在他们身上。”这对我们来说听起来很熟悉,德国之秋已经过去了 40 年。
我是人生百态,一起观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