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豆瓣4.2分的《无限超越班》已经被各大平台的自媒体创作者写到包浆。

打着“港片戏骨整顿内娱”的旗号,但是两倍速看完第一期正片,滚君唯一的祈求是老戏骨可别被内娱同化——当然,已经同化的当我没说。
少数胸怀“整顿内娱”壮志的,实诚人惠英红可以算一个。
心里话她是真敢讲。

已有6年戏龄的沈月眼神飘忽,讲自己出道6年,演的角色都比较单一;最后不忘找补,“我并不觉得这样不好,我只是想拓展一下自己,想尝试各种各样类型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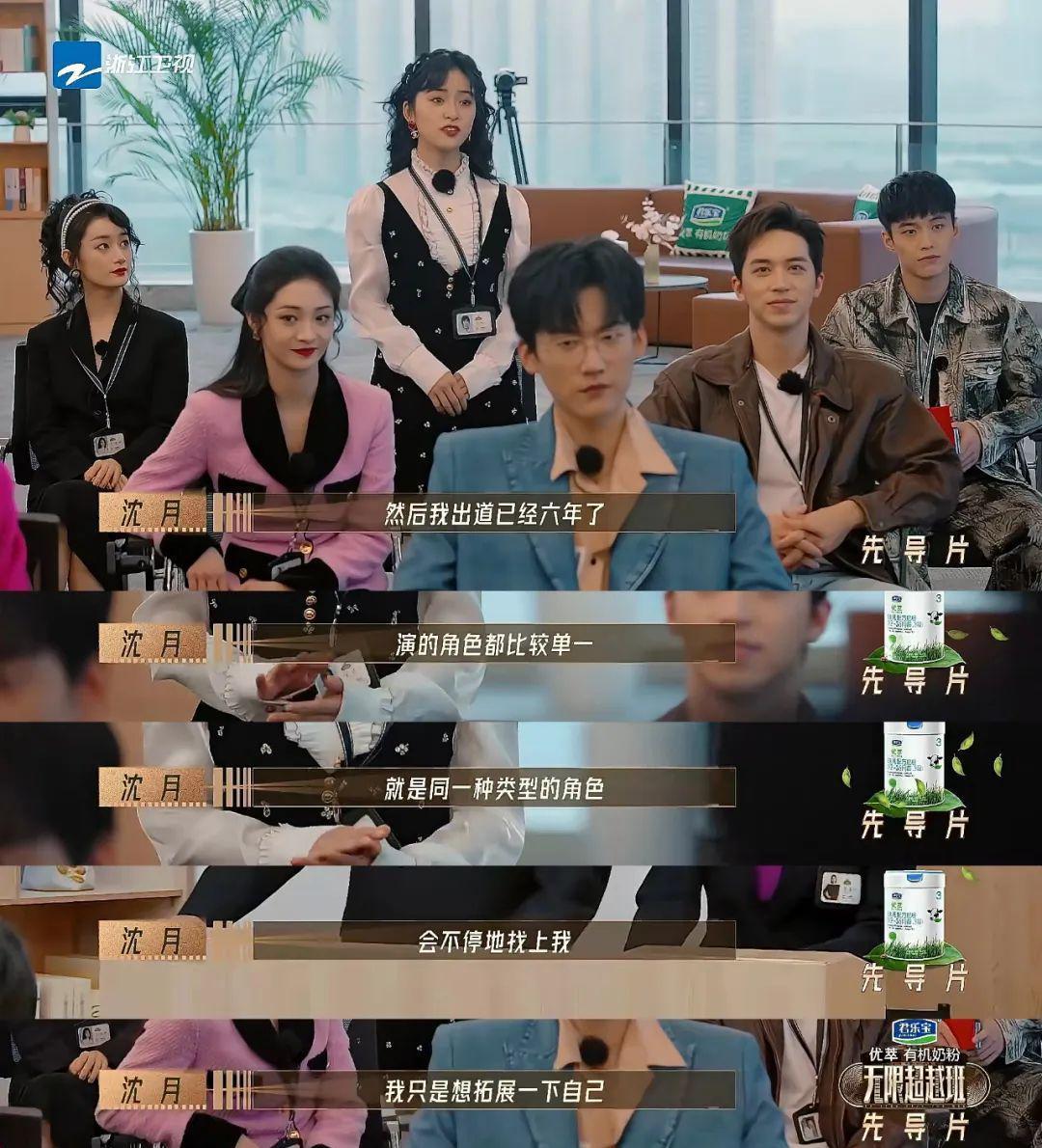
底下其他小鲜肉小花暗暗点头附和,台上惠英红直截了当,“你刚才说的话我不认同。”
“每次找我都是(演)妈妈,我都可以演不同的妈妈,为什么没有想过。”

身边的尔冬升听到惠英红的反问,就见他嘴角忽然上扬了一下,然后迅速压下去继续摆出一副假装深沉的模样。

虽然不晓得当时尔冬升想到了啥,但是听到红姐这番话时,滚君脑海里第一个冒出的,是她在接受《散步集》采访时的一段讲述:
“每个人都有他的命运。我的命运就是这样,我不会去反抗或去讨厌它。我把它给我的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这也是另一种成就。”
太多文章讲她“逆天改命”——逆天改命,夸张了。
命运给她安排的角色都是“妈妈”:
《幽灵人间》中遭两鬼上身夺舍的松仔妈妈。

《心魔》里占有欲强烈到病态的单亲母亲。

《幸运是我》中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孤寡老太。

《血观音》里将女儿视为引诱工具的冷血夫人……

不曾忤逆、没有违抗,惠英红就一个字:
“演”。
可是,她好好地在演。
命运给的一副牌,再烂她都有好好地接住,好好地打出来。
好好演戏,好好生活,好好做“惠英红”。
“邵氏打女”出道,武戏怎么打,击、劈、踢,她有自己的招式;而命运的牌怎么打,惠英红也自有一番路数。
第一步:犟。
一个纸盒,放着口香糖、一些筷子、一把敲起来“砰砰”响的塑胶小锤。
3岁多的惠英红开始学着怎么叫卖。
这一叫卖,便是10年。

在铜锣湾一伙要饭的孩子中,13岁、拥有10年乞龄的惠英红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姐”。
她本应该带着大家伙绞尽脑汁想办法赚钱,用尽一个孩童脑袋里所有的智慧,去仔细辨认迎面走过来的这个人会给我一块钱,还是一巴掌。
但是,她的目光总是不自禁地停留在湾仔电影院门口张贴的电影海报上。
那是60年代电影《红楼梦》中的演员海报,巨大的、光鲜的;海报上的人是令她心驰神往的“上等人”。
成为海报上的人,一家人便不必蜷缩进大楼旁边的楼梯底,不用再讨饭店里的剩菜剩饭吃,弟弟妹妹就有书可以读。
脱贫。
她太倔强地想要脱贫了。
14岁那年,她不顾家人的劝阻,决意应聘成为中国舞蹈夜总会的舞女;她清楚,很多跳舞的女生会被导演从那里捉去拍电影。
一年半后,惠英红从淹没于人群的普通舞女晋升为主领舞;在舞台上领舞的她被张彻导演一眼相中,试镜《射雕英雄传》中的“穆念慈”。

1977版《射雕英雄传》,惠英红饰穆念慈
第一次进入片场试镜时,她的脑子里嗡嗡地重复着一句话:我必须要做好。
一定要做好。
做不好会被淘汰,会不能出人头地,会摆脱不了贫困。
新人第一天开工,很多其它棚里的人都来凑热闹,他们小声议论着:这个女孩真的从来没拍过戏吗?
第二招:抓 。
机会是会溜走的。
每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她都必须死死抓住。
《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这块饼原来落不到惠英红的头上;但是,原定的演员弃演了。
在试镜的六人中,惠英红表演吸睛、体态轻盈、丝毫不怯场。
更何况,她还是个美人胚子。
本来只是试镜梅超风众多徒弟中的一个,却被张彻导演钦定为《射雕英雄传》中的第二女主角“穆念慈”。
1979年,惠英红拍了个电影,叫《烂头何》。

原来她只是一个小配角。
小到镜头一扫而过,可能都看不清楚她的脸。
当时的女主角在那场戏里打完第一个镜头就偷偷落跑了。
情急之下,被刘家良导演认为“会打”的惠英红只得装扮上阵挑起大梁。
其实,刚刚入行,她哪里会打?
虽然不是很会打,但是她不露怯。
毕竟舞女出身,动作身段都比较灵活;惠英红的武打戏,一拳一式都带着舞蹈的韵律。
整个拍出来的时候,人家都觉得:真的从来没见到刘家良他拍打有这个风格。
《烂头何》之后,刘家良导演为她量身定制了一部电影《长辈》。

1981年电影《长辈》剧照
1982年,在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惠英红凭《长辈》获最佳女主角。
她云淡风轻地走上台,就讲了三句“谢谢”。
第一位香港金像奖影后?
她不稀罕。
掂一掂手中的奖杯,她在想这奖杯是不是金的,能不能卖钱?

幸运的是,《长辈》达成了惠英红的执念,扭转了家中贫困的局面。
她也从每个月只能拿500块钱的人工费变成每部电影都可以分红。
拍了十几年的打戏,可以说每一次开工她都会受伤。
韧带断了一半。
膝盖骨头碎裂。
还有一场戏,是要求她从四楼直直地跳下来。
底下铺了榻榻米,还有一层纸皮盒。
原定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纸皮盒上;可是她太轻了。
只听到“咔”的一声响,骨头断掉了。
被抱着去医院,去拍X光,医生说要打石膏,两个小时。
但是剧组一直催。
惠英红不容许自己眼睁睁看着机会溜掉。
石膏也不打了,直接被武术指导抱到现场。
她就坐在武术指导的两手之间,上半身还在打,下半身两条腿轻飘飘得乱晃。
至今,惠英红的两条腿都是一长一短,常常会觉得腿好疼。

第三式:舍。
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武打片逐渐落寞,文艺片大行其道。
如果她甘心于只做一个“打女”,她会是全香港最卖座的动作演员。
可惜又可喜的是,她不甘心只做一个落寞的“打女”。
她要转型。
但是谁敢冒险用一个动作演员演文艺片?
1988年,入行十四年的惠英红割舍了自己的舒适圈,自费10万港元远赴法国巴黎拍摄艺术写真。
虽然是凭“武打女仔”闯出名号,但是首先,她是一个女子,还是一名风情万种的女子。
她可以转型。
文艺片的时代来了,她照样能挑起大梁。

拾阶而上。
微卷的头发散落在赤裸的肩头。
蜜桃似的臀部翘起圆弧的曲线。
黑色丝袜。
高跟鞋。
留给看客的只有背影。

落地窗旁。
天鹅似的颈,凹凸有致的锁骨。
一字肩的黑色纱衣,绷得紧紧的黑色内裤,被夕阳的余晖映照成暖黄色的皮肤。
慵懒地倚在窗框上的惠英红,成熟女子的风情被镜头无限放大。

整本写真集中,最性感的莫过于她身披薄纱,全身赤裸贴在玻璃上的这一张。
姿态甚为撩人,眼眸却很纯粹。

与日本女星不同,大部分港台明星从未出版过官方写真集。美丽的胴体大部分都是被片场或者狗仔的镜头所记录。
连拍摄性感写真都兢兢业业,要求自己身材达到完美状态;并且自掏腰包出版性感写真的中国女星,惠英红还是少数。
惠英红不是天生的打女,也并非天生便能将“命运给她的一切安排得好好的”。
打拼十余年,分明是第一线的武打女演员,拿到手的剧本却都是让她演三流的小角色。
《惠英红巴黎写真集》的出版也并未帮她成功转型,反而让她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
巨大的落差,她安排不好。
别说安排,惠英红连接受都接受不了。
她好像病了。
落魄。
惶恐。
抑郁。
和朋友混一起整夜打牌,打到天亮。
开车回去时,惠英红无意间望了一眼后视镜,被镜子里又油又黑的一张脸吓了一跳。
她想这样一辈子是不行的——回去演小配角么?
可是她做不到。
于是,她开了美容院。
一整天儿都在那里低三下四,向医生赔笑、向美容师赔笑、向客人赔笑。
生意没有能做很久,惠英红把店卖了。
自那以后,她一门不出二门不迈。

一次,她将自己反锁在三楼的房间里,将手提电话关机后,服用了安眠药。
等妹妹破门而入的时候,她已经口吐白沫躺在地上。
再睁眼的时候,惠英红身上湿透了,她看到妈妈和妹妹,眼睛都是红肿的。
她的第一反应,是后悔、是难过。
她不相信惠英红会做这样的傻事,但是,病了的惠英红也许会。
于是,她拉下脸去看医生,吃药,吃了九个多月的药。
她想,往后的每一天,每一天的时间,她都要好好活着。
慢慢地,她去见TVB的最高层,拉下脸去求一个演戏的机会。
主角,配角,她不挑了。
惠英红说:“那后来,陆陆续续就有(一些角色)啊,电影也有啊。”
“其实命运对我挺好的。”
曾经,命运馈赠的礼物,她好好地抓住了;如今,命运给她摆了一道,她也好好地跨过去了。
《无限超越班》中,惠英红将炮筒瞄准40+女演员的转型难题火力全开。

有观众埋怨,她较真、刻薄、爹味太重。
但是,我看到的惠英红,好真诚的一个人。
不惜亲自将结痂的伤口血淋淋地破开,劝阻后辈不要步我的后尘。
她唯一做错的,或许是她不应该在这档笑话似的综艺里自揭伤疤。
一辈子的痛处被看客轻易地当成了一个乐呵。

到了如今这个年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华,她见识过;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凉,她也经历过。
除却演戏,她会煮饭、爱整理,打毛衣、绣花,她都懂。她会画画,愿意关心也懂得怎么照顾别人,还考了专业按摩治疗师的牌照、心理科治疗牌照。她也曾进修过医学科,小病小痛她也可以解决……
惠英红说:“我是打不死的。哪怕在人生的最低潮,我也能够找到自己的空间生存。”

2022年,每个人都不容易,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生存的位置。
在魔幻的现实中,请将自己安排得好好的。
我们都要将自己安排得好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