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故事本身就带有着浓厚的后现代色彩,个人冒险、信仰寄托、宗教情感以及灵性体验等元素都弥散在故事之中。为了将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元素融入真实的环境,以“身临其境”之感表现出信仰与情感的力量,李安选择了立体摄影技术。
技术的选择其实在客观上呼应了海德格尔“技术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的观点,“技术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现象,在本质上比作为主体的人更有缘构性,也因此更有力、更深刻地参与塑成人的历史缘在境遇”。

将技术作为揭示此在在世境遇的解蔽方式,这样就最大程度上规避了技术滥用而生成的“视觉奇观”。通过恰当的立体成像与虚拟现实技术,呈现一个由光影穿梭形成的观众与影像、现实与幻境共生的完整的“电影世界”。
有学者指出,“电影所意指的‘电影世界’均由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共同构成”。银幕上所呈现的包括文本、移动图像、声音在内的全部画面,组成了电影世界的可见物。

而在画面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具有“指示性幻觉(referentialillusion)”意义的“世界”,它并没有实际的投入到拍摄中,而是由一些银幕内隐含的设定来刻画的。
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在电影中彼此交融、互相阐释,使得“电影世界”的呈现显得越发的真实可信。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李安用立体视觉技术让电影的“不可见者”展现在观众周围。

如果说在平面电影时代,电影已经借由水平的二维银幕创造出无数诗意与优美的“视觉奇观”,那么数字立体技术的介入则为电影在银幕水平维度之外,增添了向银幕内无限延伸的垂直维度,它们与观众的视听感知相融合形成多维的立体向度。
立体成像在营造故事气氛方面确实比平面成像时期技高一筹,在如梦似幻的人造巨型水域中,李安通过大远景,将派与老虎面对无限自然的渺小无力之感尽现眼底,同时,立体视觉技术通过深度和会聚度的纵深效果,将观众拉进叙事所指的“虚实共生”的“幻境”,让观众在真实与幻觉的交织中与派“共生死”,体验超现实景观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派的恐惧与绝望。

在脱离了平面银幕的横纵坐标的制约而成的立体视觉空间中,镜子般的水面、辉煌的落日被赋予了独特的“光晕”意味,并生发出新的精神维度。
在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光晕是一种“时空的奇异纠缠”,它产生于原初世界,是一种自然生发的生命之光,是处于现实世界的人们心之所向。光晕具有“此时此刻”的在场性,“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

对于艺术作品而言,“光晕”指的是艺术品内在的生命气息以及所散发的生命的灵韵。本雅明指出,“仪式”对于“光晕”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艺术作品一旦不再具有任何仪式的功能便只得失去它的灵光(光晕)”。
可见,对于宗教和仪式的膜拜使得光晕在“在场”之外,又增加了一份“神圣”的维度。由此,艺术就不再是事物的表象的还原,而是内在地散发出自身固有的“神性”的生命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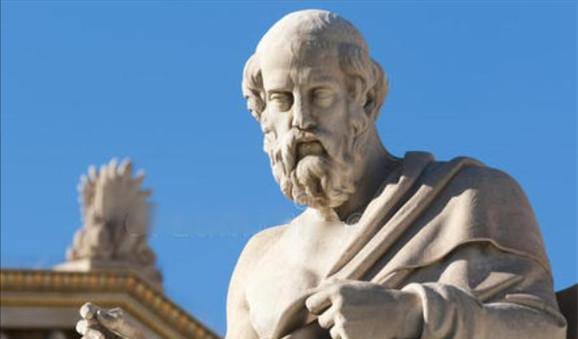
《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光是视觉的中介,而夜则模糊视野”来表明自然的明与暗与人的精神之间的相互交融。
电影中,当派孤独地站在救生筏上,他的四周是一望无际平静的海面,阳光从他的头顶洒落,光与影的变换不仅形成一股静谧超然的氛围,也赋予画面一种宗教感与神圣感的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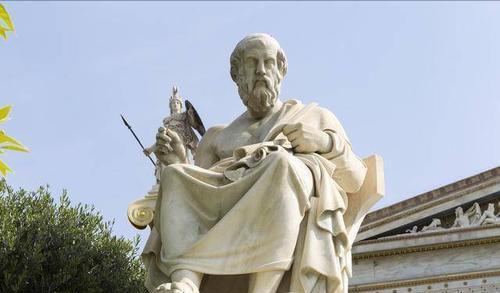
立体成像技术所形成的是一个绵延、崇高、广博与深邃的,具有无限延伸性的的诗意空间。正如巴尔塔萨所说:“光辉是一种垂直限度的无限深度,形式是一种水平维度的有限延伸,二者垂直相交形成美(荣耀)”。
在另外一个场景中,当派和老虎遭遇风暴,一切即将坠入黑暗之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束光亮,强烈的明暗对比犹如一把尖刀,在狂风中撕扯出一道“希望之光”。

这犹如康德所强调的主体与自然较量中的征服力量,“黑夜崇高,白日优美,深沉的寂寞也是崇高的”。
派在这一时刻仿佛领悟到了宇宙中的超越力量,并在风雨中大喊“上帝显灵了,这是神谕”!电影借助立体成像的逼真的手段,不仅将夜之黑暗与光之耀眼以纵深立体化的形式呈现于观众感知,同时又借助黑暗与光亮的辩证表达遮蔽与顿悟的双重意蕴。

夜并非意味着黑暗、静止与遮蔽,而是在静止中蕴含着突破的动力,在遮蔽中寻求自我拯救与自我超越的可能。在色彩的明暗交错以及多重感知的交互下,光晕所带来无与伦比的可信性去表现超越自然科学的“神圣性”,使观众能够如同在场一般的体验派内心撕裂与拯救的强烈感受。
数字技术的精进,为视觉艺术中沉浸式的“光晕”审美嬗变提供了可能。

有学者称,“在新媒体艺术中,‘光晕’集中表现为‘媒体’与‘场所’的拟真”,立体与虚拟现实技术所表现出的具有“混合的现实”意味的“场”使得机械复制时代的“非在场”“复制性”的“光晕”转向四维甚至多维空间形式下“沉浸式”的“光晕”体验。
在影片浮岛的段落上,“光晕”也承担整体美学意境体现的重要作用。当夜幕降临,水面上漂浮的海洋生物仿佛为平静的海面增添了一簇簇柔亮的光,派俯身海面,看到了一个奇异又绚烂的“海底天堂”。

在这座看似静谧富饶“海底天堂”里,李安通过将汪洋、扁舟、猴獴、飞鱼、星光等看似简单的空间元素,通过整体性的审美构图展现为一个可以被真真切切感受到的充满“光晕”的幻境。
对于这些具有“光晕”效果的素材的选取,李安是非常挑剔的,在他看来,戏剧化素材的选取和组合应该能够检验人性和神性。

因此,在段落的处理上,李安不仅沿用了一贯的唯美与诗意的影像风格,通过计算机运算所生成如镜的海面与如画的星空,以及种种现实海岸线所存在的自然景观,展现出一副静谧、具有感染力和诗意画卷。同时,在视觉接收上也呈现出就具有“沉浸式”的“在场”体验。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视觉效果总监比尔·威斯登霍佛也曾说,“我与特效部门全员的终极目标,就是让大家感觉我们什么事情也没做”。

拟仿的真实感与光与影的纵深感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亲身般地感受到电影所生成的那“形成于我们梦想中的”的“如幻、如梦、如影”的宇宙奥秘。
当然,技术的介入不仅在明暗交织、纵深交错的影像中生成如梦似幻的“沉浸的”现场,同时,也使得电影所“创造的世界”具有了更广阔、更深邃的意蕴。

李安在构想这部影片时,就曾指出“电影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艺术,有着其媒介特性下不同于理性的接近无限的方式”。
它不仅可以将“无限”转化为一个包含着开始、过程以及结局的完整的故事,它还可以通过象征和隐喻等电影修辞手段,来“窥探”那些令我们恐惧却又不断吸引着我们的非理性与未知。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数字技术使影像所指的那个世界以沉浸的方式进入观众的感官,并透过技术将过去与未来呈现于当下,逼真地描述科学上无法存在的事物。这种类似于德里达语境中的“幽灵术”一般的电影技法不仅激活了经验,也激活了自身。
影像所叙述的世界是虚构的世界,然而“虚构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纯粹自由的,想象中的世界”。借由数字技术,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经历的世界,在影院的空间环境中被无限地打开、无限地扩大,形成了一个比真实还真实的,“不符合日常逻辑,但却逻辑自洽”的“幻境”一般的“无何有之乡”。

可以说,借助数字成像技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达到了鲍德里亚意义上“某个深度真实的反应”和“神圣秩序再现”的电影“意识拓展空间”探索。
一方面,数字技术所生成的空间突破了胶片时代的横、纵双重维度的平面空间,而指向了具有更深邃、更悠远的纵深立体空间。在具有流动性的空间里,“光晕”被解放了出来,并生发出在“去魅”的时代重新叩问神圣的意义的精神向度。

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的美与真在于蕴含其中的具有宗教意味的自由性,“只有在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
另一方面,在强大的数字技术支撑下,“消失的摄影机”使电影制作摆脱了客观时空的束缚,所生成的是在“现实”的边界上诗意延伸出的具有高度虚拟性与复杂性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仅是新技术和视觉元素的集合,更是连结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融汇了现实、梦境与幻觉的,“包含着超越现实、建构理想的可能性,促使观众重审理性、改变自我的思维方式”的虚实共生的“幻境”。
